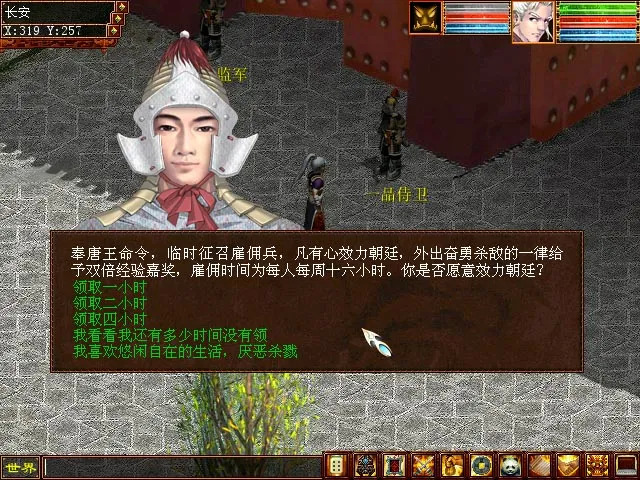游戏论·文化的逻辑丨机制与意义:作为数字现实的电子游戏
本文的第一部分
我们着重指出游戏进行时,参与者在现实中的活动与感受。特别是研究《The Witness》,把其创造的“虚拟”场所看作一个确实存在、具有物质感的数字场景,同时将玩家“主导”的角色看作用于与这个数字场景沟通的数字工具。怎样让数字的实在性与新兴的物质观进行系统化阐释,并使其超越单纯的辞藻堆砌?我们有必要构建一个与既有认知迥异的物质性新框架。电子游戏的虚拟世界确有一番独特的物理属性,它不同于现实生活,能具体地揭示物质世界的丰富维度。要明白这种多重构造,我们先稍微偏离主路,谈谈信息如何能成为物质的一种形态。
信息之为物质的可能
依照旧有看法,资讯必须依托实体媒介,资讯仅是物质的一种属性,并非物质本身。不过,依照物理学家文小刚揭示的某种自然推理方式,倘若进一步探究物质的来源,那么“物质承载信息”这一说法所隐含的意义是,其中提及的“信息”仅涵盖了物质的部分特征,物质还存在其他未被揭示的特性。倘若仍旧探究那些尚未揭示的特性根源,我们便可能面临两种困境,或是无休止地追溯,最终将终极的物质本质归结为未知;或是认定一种终极的、可被描述的物理构造,即便我们未必能找到这个终极构造。假如这个构造确实存在,那么对它的数学刻画就不再仅仅是理论框架,而是直接对应着真实世界,否则任何未被说明、未被系统化的部分又会变成一个实质性的未知领域,换言之这种说明依旧不是最终的物理构造。在这种看法下,物质在根本上源自于信息或者构造。虽然我们无法认定这种根本构造的真实性,不过当前物理学学说已持续把人们生活里感受到的物质形态,剖析成信息或是数学构造。比如能量这种以往被当作物质特性的概念,在量子力学那里被看作是粒子的振动频次。而且,在超弦学说里面,各种基础粒子都源自称作弦的一维构造的不同振动形态。
信息科学方面,元胞自动机与计算宇宙的实验提供了一种参考方法,具体涉及从前者到后者的探索过程。元胞自动机是宇宙计算的底层结构,属于时空均离散的动态演化体系,常以正方形、三角形等维度的立方体格网作为基础,这些格网被称为“元胞”是系统的基本单元,它们以特定方式排列,每个单元包含若干种状态,最基础的状态表现为开/关或黑/白两种形式,本质上是一种二进制机制,元胞的状态会按照既定法则随时间流转而改变,这种自动机能在计算机上高效模拟成千上万代,从而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元胞自动机最初由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构想出来,他的想法源于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与瓦尔特·皮茨(Walter Pitts)对神经系统开关特性所做的工作,他们研究的是神经元的开启与关闭机制,冯·诺依曼将麦卡洛克—皮茨神经元系统当作一种计算设备,并据此构建了具备类似逻辑性能的切换装置。从另一角度来看,诺依曼觉得神经体系也能当作一种图灵机来看待。当他察觉到生命体与机械装置间存在这种相似之处时,诺依曼构想了种能够自我繁衍的自动装置。他的同事,数学家斯塔尼斯洛·乌拉姆提出,自动机无需考虑构成材料,仅保留抽象的网格即可,这样的网格能够充分表现状态的变化过程。诺依曼最终选定了一种拥有二十九种状态的二维元胞自动机方案。此后,元胞自动机的研究产生了诸多引人入胜的发现,约翰·康威于1970年推出的数学游戏“生命”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实例。该游戏属于一种二维自动机,其运行空间是一个由方形网格构成的平面,这些网格即为其基本单元。每个单元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即“存活”与“消亡”,有时也被形象地描述为明暗两种色彩。每个单元都有邻近的八个方块,它的情形转变遵循这些准则:当一个单元的邻近区域中有三个单元处于活跃状态时,该单元在下一时段将变为活跃;当一个单元的邻近区域中有两个单元处于活跃状态时,该单元的状态将维持原样;在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的所有情形下,该单元在下一时段将变为非活跃。根据这些准则,机器将能衍生出许多繁复且具备规律性的形态,图示中那个备受关注的“滑翔机”便是其中一个较为基础的范例。单元的形态展现开yunapp体育官网入口下载手机版,以四个时段/轮次为循环反复,每隔四轮,机器便会重现先前的图形,只是向右下方偏移了一单元格,整个演变过程仿佛一架滑翔机在移动。“生命”游戏中还会见到“滑翔机枪”“旅行者”“蜘蛛”等更加复杂的构造,无法一一枚举。
生命模拟中的飞行器(源自混沌至秩序,珀塞斯出版社,1998年约翰·霍兰德)
一种精妙的动态现象源自基础的运作准则,众多探索者本能地觉得,该类体系能够说明自然界里生命繁衍与衰退的现象
美国学者凯瑟琳·海尔斯在其著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通过刘宇清的译文,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17年版第324页提出观点,该观点指出后人类概念的复杂性,并分析了科技发展对人类身份认同的影响,同时强调了文化因素在塑造未来人类形态中的关键作用,这种观点对于理解当代社会转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史蒂芬·沃尔夫勒姆于1983年建立了一套名为“Rule 30”的规则体系,他深入探究了一维元胞自动机的运作机制,并且将它的运行产物进行了归类,归类结果涵盖了几种不同形态开yun体育官网入口登录app,具体包括完全一致的状态,彼此独立且循环重复的结构,毫无规律可循的混乱模式,以及带有局部特征的非简单复杂结构。沃尔夫勒姆发现这四种模式与动力系统中的四种模式有相似之处,前三种分别对应于趋向于极限点,趋向于周期,以及与奇异吸引子相关的混沌现象。这种复杂模式属于特殊类型,它的暂态过程特别漫长,时间跨度很大。此类模式具备执行处理的能力,并且能够完成各种复杂的计算任务,甚至能够实现全功能运算。朗顿在其研究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元胞自动机执行特定功能的情况,这种功能涵盖数据的传送、保留以及更正,并剖析了实现这些操作所需满足的必要前提
克里斯·G·兰顿在《混沌边缘的计算:相变与涌现计算》,发表于《物理D》1990年第42卷第12至37页的文章中提出观点
这表明抽象的运算能够从自动机的运作中自行产生。与此同时,纷繁的自然景象乃至生命活动,包括人的举止,都可以看作是某种计算活动。沃尔夫勒姆主张,自由意志的成因在于“推算未来须耗费巨大运算力”——即便世界的基本法则非常单纯,其衍生的人类活动却异常繁复,两者间的运算差距无法缩小,人们观察某人实施极为繁杂的举动时,会说他仿佛在做出决定,因为无法预知他最终会怎样行动。倘若我们果真能构建出宇宙的完整图景,万事万物皆可量化推演,所有物理学上的困惑都将简化为数学的范畴
(果壳网专访)斯蒂芬·沃尔夫勒姆:宇宙的本质是计算
爱德华·弗雷金提出了看似更为大胆的观点,主张宇宙可视为计算机执行的程序,这是一个运算/信息流程,而驱动它的设备与该流程独立,我们既无从知晓其构造,也无需探究。
元胞自动机的研究及其计算模拟开元ky888棋牌官方版,对宇宙认识和涌现概念产生了作用,进而波及众多科学分支,特别是那些研究复杂体系的学科。这种效应也传播到了文化研究范畴,然而类似弗里德金那样较为极端的见解,特别是主张物质现象在某个维度上完全由信息主导的观点,并未获得普遍认同。后人类学研究者海尔斯认为,像元胞自动机、计算宇宙这类实验,是控制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浪潮中的关键探索,不过她对把所有宇宙现象都看作是“纯粹的二进制信息形态”这一观点,抱有审慎的看法。她觉得弗雷金主张我们永远无法探明宇宙计算机的实质,而我们仅仅是宇宙计算机中运行的程序,这种说法已经把终极物质的具体形态排除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外
美国学者凯瑟琳·海尔斯在其著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阐述了后人类主义的核心理念,此书由刘宇清翻译,于2017年在北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325页的内容尤为关键
实际情况是,海尔斯并未准确把握弗雷金的观点,弗雷金真正着重说明的是,应当将整个物质世界看作是一种信息机制,假想一台能够处理该机制的装置,仅是一种便于描述的比喻手法,即便存在这样的装置,也完全不会改变信息机制(也就是物质世界)的样子,它始终存在于某个不可及的地方
【什么是计算?(自然)如何进行计算?】
文小刚和弗雷金的主张,都没有否认宇宙及物理现象的实体本质,反而提出了物质性的一种潜在成因——普遍认为物质现象的产生源于更基础的资讯构造,而我们针对现象的审视(特别是普通情境下)常常会忽略某些构造,正是这些被省略的、未明确阐述的部分构成了物质层面的未知领域。海尔斯无法摆脱信息或形式必须依托实体存在的固有观念,未能超越信息与物质之间的绝对界限,反而把物质属性看作是虚无缥缈的神秘想象。
多层次的物质性
对宇宙的探究和对新现象的思考也促使物理学界探究物质的基本构成。约翰·惠勒在1989年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万物源于比特”,这个精练且富有深意的说法既指出了物质源自信息的观点,也暗示了新事物出现的可能性。惠勒在此处所说的“比特”,并非指代普遍的数学构造,而是特指其字面含义所包含的0与1这两种情形。他的思想已经十分接近计算宇宙的生成方式,在他构想的体系中,对量子态的审视即是对于基本单元量子比特状态的决定。所有物理特性,包括宏观层面的现象,均源自量子比特状态的产生。